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蒋捷的词,觉得词的画面感很好,词中见画,别有韵味。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中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,这几句几乎被我用滥了。
其实,在不太懂“流光”这个词的时候,我早就知道它的学名——时间。但是文章拟题的时候仍然喜欢用“流年”、“流光”,就是钟意这两个词的画面感。“似水流年”多形象!“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”多具体!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爸给我解释时间,让我第一次对时间有了深深的敬畏。他说:“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,它就在走,永远回不来了。你刚才洗了脸,可是你明天再洗脸的时候已经和今天长得有点不一样了,你在看不见的地方偷偷长大了一点点。最后你会变成大人,老人,那时,爸爸妈妈也许就不在了”。我当时小小的心灵充满了悲伤,爸爸妈妈没有了我怎么办?那我是不是也会死掉?死是不是很疼?慢慢我开始明白,对于个体,时间不是海洋,而是江河;不是固态,而是流体。它是有尽头的。
因为人类对时间的敬畏,所以发明了种种节约时间的好东西。车子就是。先是自行车,后来又有火车,汽车。高铁尖厉的呼啸和F1赛车车轮所向披靡的速度表明人类追赶时间的脚步越来越快。没准儿哪天“和谐号”就超光速把时间“和谐”了。“流光”就成了莫奈笔下的《日出印象》,凝固在人类的画布上了。
时间贵得没人买得起,但是车子也好贵啊。尤其是在我们小时候,中国人买不起小汽车,大街上的公交车都很少。那时候,“轮子上的中国”指的是自行车。
我小学就学会了骑自行车。但是因为在三线厂区生活,我从没有过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经验,所以我的骑车技术就像在驾校的路上开车一样,能走,但是千万不能遇到人车拥堵。若是这样的司机就叫马路杀手,只不过骑自行车的马路杀手多数的时候是自残。
我们读大学的时候,天津绝对是个自行车王国。但是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,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,给读书的孩子买自行车的也不多,因为买自行车不仅得有钱还得有自行车票。加上我们班外地同学多,所以天津同学的自行车就成了香饽饽。现在想想,那时候他们真大方。
我借车的时候很少。因为第一学期的冬天就差点被自行车弄了个“半残”。学校在北郊区,外地生取家里寄的生活费要到很远的北仓镇邮局,从进校开始,我每个月借一次车取钱。直到那年的白色圣诞节,虽然室友警告我,说雪天路滑,但当时刚下雪,松软的地面踩起来的好感觉没有让我警醒。作为从来没看见过雪的南方人,我没有领教过雪的厉害,于是自信满满地骑上车了,刚骑了50米我就摔了个大马趴,我根本没当回事儿,心里满满的就要过上好日子的幸福感。还没到校门口,第三个大跟头终于让我知道,我的骑车技术肯定得“让我装逼,让我飞”出去。只能老老实实推着自行车回宿舍,把取款单交给男同学,请人家帮我取。从此,我在大学期间就没怎么骑过自行车。
大学毕业后,我家买了个自行车,但是我很少骑。生活在东北,有小半年的时间是冬天。在冬天骑车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勇气,两者我都不具备,所以我始终都是坐四个轮子的车,眼前的苟且和心中的远方都交给公交车、计程车和私家车了。自行车渐渐远离我的生活。
我的骑车技术从大学那一场雪后,一下回到解放前,此后的骑车技术只限于在操场、广场这样的地方溜达。
虽然没去蓝翔技校,我也有机会把骑车技术重新捡起来。在上海给女儿做陪读的时候,每天要到菜场买菜,我买了个自行车。第一次骑上路,过十字路口,没想到遇到完全不遵守红绿灯的摩托车,本来手就生,心里发慌,看到横冲直闯的的摩托车自己就先翻了。自那以后,我就天天推着自行车买菜了。骑车技术又丢到爪哇国去了。
哪儿成想,30年后我这个资深菜鸟还能以骑车的方式纪念我的大学生活。
作为这次餐旅86相聚30年的主要活动,冯益军和他的润茂骑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安排了自行车骑行活动。我戏称这是冯益军任制片人、回得斌和黄德宁导演的一部大片,片名叫《纪念我们自行车上的青春》,我们每个人都是主演。润茂公司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部赛车。先用汽车把我们拉到北辰公园,在专门的自行车道骑行15公里,再由汽车把我们送到五大道的聚餐地点。冯总想得真周到,早就知道骑车技术比我强的人虽然一大票,但水平高出我也就一丢丢。毕竟这么多年大家多是以汽车代步。
9月10日早上八点半集合,出发到北辰公园。天气真好,早上还明晃晃的太阳,待我们骑行的时候躲到云里去了。装备也好,赛车带变速调节的,黄德宁设计的自行车服为我们的颜值加了不少分。后勤也好,有教练陪伴,还有专职摄影抓取精彩镜头。道路也好,路上行人不多。风景也好,“一堤柳色,人在画图行”。
只有我骑得不太好。我从来没骑过赛车,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骑过,但显然他们的技术和胆量都比我强。虽然有教练教授技巧,也一路随行,我还是最后一个才把车骑走的,并且一路磕磕绊绊。最后到终点时,看到那么多人,心里一发怵,不知道先按刹车闸把车停下来,直接就用脚当刹车片,我的胳膊腿当即就摔成调色盘了。
尽管如此,我和大家一样,认为这次自行车骑行是我们这次餐旅86相聚三十年最有意义的活动,没有之一。
我们的大学时代,曾经每个男孩子的自行车后面都坐着一个爱笑的姑娘吧?曾经每个姑娘都羞涩地伸出双手抱住前面那个男孩子的腰,靠在他温暖的后背,相信他会将自己带往那个叫幸福的地方,甚至也许幻想过一家三口骑在一辆车上的画面。因此,用自行车骑行来重谱一曲青春之歌再合适不过了。曲远歌长,曲虽然是新曲,调却是老调。就让那些青春的流光,在岁月里辗转了吧!我也曾美好!我依然将美好!
如今,当年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每天手握方向盘,仍然用车轮丈量着生活,心中却不再寻找那个幸福的终点站,只要沿途仍有风景,就值得我们上路。人生的风景不只有青绿,还有金黄。我们人生的车轮已经走过稚嫩的春,喧闹的夏,走到了成熟的秋。我们都生活在眼前的苟且里,却仍然热爱纵横驰骋在远方。
蒋捷的另一阙词《虞美人·听雨》调子有点儿灰,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”,的确,三十年来我们都有痛苦的完全否定自己的时候,有看着天空一片灰暗的压抑。但是,当大学同学再聚的时候,发现我们依然可以眉眼弯弯,言笑晏晏。因为我们小时候有句名言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。还要啥自行车啊?
不过,大方的冯总真的送了我们每人一辆赛车。

微信扫码查看本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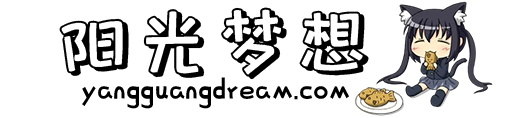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