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雪!清早,院子里就有声音。金丝鸟穿过梅花,也穿过飘落的一场雪,以雪激活了眼睛里有些僵直的一个个语气词。
走在大街上,大街平素绷直了的线条显得有点模糊,迎向两旁建筑修订的镜框,空中飘下密密匝匝的雪花,一切可以给出的答案因隐而显,问题是我们又能明了多少呢?看那些伸出双手的人们,是否和我一样虔诚地接受一个悬了很久的答案?
雪里,并没有发现雪的具体,一向我不认为雪是一个简单、直白甚至单调的名词,我更愿将之视作一个形容词或虚词。它不需要其它定语来修饰自己,只要足够的冷、有一点儿空间,不需要时间。当你走入其中,你即能感受到雪,应和着你的一声声叹息、惊讶、欢呼,作为你的背景占据了你内心的天空,遮住了你在悲伤、孤独、忧郁前加注的修饰语。
顺着街道走下去,远处是雪,近处也是雪。随着远和近展开的雪景、打开距离,往山上走去。那些石梯像是知道我要来似的,用比梯子本身更宽的宽度延伸于脚下,山间的钟声夹杂在飘雪中,打在衣服上、脸上、头顶,又顺势滚落,一种清脆的声音布满林间、路面、草丛、屋顶、远天。
雪,时急时缓,下得缓时,天地仿佛也安静下来,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停下来静静地注视着雪的飘零,反之,又似这雪在深情地凝注着世间的有情与无情;下得急时,你可以听见行脚者划亮的霞光、踩响的经卷,如是阐释的雪更符合于雪的洁白,更合于我们仰望的高处的美好和完整的存在。
来到寺内,我突然觉得飞雪过眼的佛像凝固了雪,那么形象、生动,或者说如果有一个可用来表达雪全部的实在和抽象的词,恐怕莫如“佛”合适的了。站在佛前一下子觉得自己一直都在雪中、一直都在佛中,好吧!是佛的抽象的雪将我们覆盖、唤醒,将我们从“我”这个顽固的实体里牵引出来;是雪的形象的佛让我们感觉自己的存在,给了我们照见的镜子,一面、两面、三面、十面……无数面,无数的形象包围着、无数的雪花飞舞着、无数个我分解着镜子之形、镜子之态。
大殿前,雪下得正当时,来者和去者相逢于此。僧人、信徒、观光客及应景应时的人们,他们拍照着他们也不清楚的雪的世界。当然,我也在其中,我注定要在其中的。
“欢迎赏雪,免费品茶!”一个黄衣僧人殿门内走出,招呼着我及我们,招呼着不动的“我”和他们。大殿旁的观景台为眼睛设置了位置、收集了风景,也为风景拉开帘幕。
突然记起这黄衣僧人来,以前,每次来寺里,总见他跪在大殿上,大概七十多岁吧,面前一张普通的书桌,桌上放着一本大字诵读本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,右侧放着一只木鱼。一边用木棍敲着木鱼,一边读诵佛经。
此时,见他出来,我忍不住打量殿内的佛像,只见佛之金身映照出一大片飘落的雪和门前张望的我。好大一场雪啊!寻声望去,佛旁的阿难嘴角动了一下,回头却见黄衣僧人(说僧人有点远,称黄衣老人则近,雪也格外近)脸露笑意。
“是啊!好大一场雪!”我们一起见于一场雪。
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是同一条路,迎我上山的是雪,送我下山的也是雪,它以一场雪的形象迎我上山,又以另一场雪的风景送我下山。
2016.01.23

微信扫码查看本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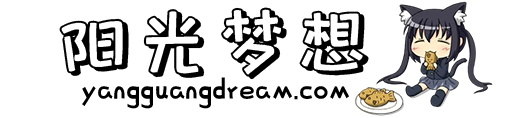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